来源:济南稼轩学校 作者: 李秀伟 已有0人评论 2018/10/31 15:43:59 加入收藏
视频观看密码:2018
| 下载信息 [文件大小:13549 KB 下载次数: 次] |
教学改革的背景,从科学革命以来,大致经历了三场与时偕行的转换,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变化在自然发生。
由于现代知识的批量生产以及对机器大生产的适应,教学沿着“从知识到知识”的程序性道路,让学生把知识学会,用来考试,用来应对相对确定未来生活;近三十年以来,伴随着新兴知识经济的发展,人的未来开始进入不确定性时代,知识本身价值受到挑战,教学开始进入“从知识到能力”的时代,知识不是不重要了,而是知识要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生活化,知识已经无处不在,但是,需要警惕,没有基本的素养,就找不到你想要的知识,于是,我们可以说,未来教学将会进入“从素养到知识”的时代。

素养是什么?就是在真实情境中的人的认知经验和敏感性。那么,在学科核心素养时代的教学应该建立怎样的时间逻辑呢?我们从“问学”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与现代教学相比较,逐步建构起了向真实情境发问的课堂逻辑。
一、从“伏羲问自然”到“我问人工智能”
这个标题很奇怪,七千年以前上古的伏羲和今天的智能社会有关系吗?关系在哪里?即便是有关系,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学校教学有关系吗?
我们看看伏羲八卦的由来:
伏羲时代的上古,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人们靠打鱼、狩猎、采摘过日子,外出最怕天气骤变,大家知道伏羲能够预报天气状况,就纷纷去问,伏羲预报的非常准。于是,来问的人越来越多,人多了以后,伏羲没有那么多时间应付,怎么办?他就说:“从明天开始,我就在这棵树上挂一个‘☵’的图像,就表示明天天气是雨天。”这就是“2•1•2”代表水、坎,也表示雨;“1•2•1”表示火,“2•2•2”表示地等。
再后来,来百姓对这些“二进制”的数字背来背去还是觉得麻烦,就问伏羲:“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道理呢?”这就出现了“伏羲八卦图”以解人们之惑。
这个远古的历史发展脉络给我们三个启发:
第一,道理是问出来的。
没有问就没有答,不是“伏羲好为人师”主动传授天气状况,而是当时的生活方式、生产基础、生命担忧与伏羲的思考关联起来了,如果伏羲造字,指导学习,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听、会做。这就是说,教学不是来自于掌握既定知识和规律者,而是来自于对既定知识和规律的未知探索者。换句话说,大家就都理解了:教学的发起者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可是,在7000年以后的现代教学过程中,却缺少了学习者的“问”,而变成了“师问生答”,这并不是教学的传统。
伏羲八卦的产生和“问学”相关,问学从中国文化的源始就开始了,3000年以前,文王演64卦:乾坤屯蒙需讼师……乾坤代表天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之后,就是“屯卦”所探讨的万物出生的艰难;接下来就是讨论如何教育的“蒙卦”。
“蒙卦”说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句话:“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很好懂:非我去求童蒙,而是童蒙来有求于我。
玄烨钦定《日讲•易经解义》说:“蒙虽稚昧未通,然真明内含,天良未凿,原有可通之机,一开发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终于蒙。然蒙之能亨,虽蒙者有可亨之道,亦由发蒙者得善教之宜。教之之宜何如?师道不可亵,有来学,无往教,匪我主教者先求童蒙,而强为启迪,乃童蒙虚心逊志先来求我,以决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实纯一,如初筮之诚,则宜迎其机而告之。” 有来学,无往教,这段话清晰地表述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教育方法论,老师是为学生决疑辨惑的,以学生问、教师解为基本顺序的教学之道也产生于此,是完全有别于近300年来发端于西方工业革命影响的标准化、灌输式教学的。

第二,二进制的数据思维从中国最古老的智慧到智能社会。
易经中的数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二者构成数据列队,曾仕强教授说:“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和数学里的“始数、方根、平方、立方、四次方、五次方、六次方”以及2n里的“n=0、n=1、n=2、n=3、n=4、n=5、n=6”是一致的。所以有人认为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二进制数学思维,以及最后带来互联网革命的数字技术,是受到易经的启发,互联网、智能社会的智慧就是易经“数”的智慧,虽然多多争论,但不变的事实是:易经生生不息的数学思维、数据思维与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发展有着7000年的遥相呼应,所以,伏羲八卦到智能化的社会之间,从数论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
传承到今天,人类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人类爱机器开始胜过爱彼此吗?恋爱真的不如手机重要了吗?
货币真的会消失吗?铜臭气、见钱眼开、拜金主义这些词汇会让年轻人不知所云吗?
机器比人更了解人吗?人会被计算出来从而成为“人机器”吗?
机器人的深度学习会颠覆人类吗?学习已经不是人所控制的了吗?
终极之问:人会成为无用的大多数吗?如果会,做好准备了吗?
赫拉利说:饥饿已经不可怕,瘟疫已经不可怕,战争已经不可怕,甚至生老病死也已经被战胜。在智能化的社会里,我们突然发现,人正在失去学习的特权,人的学习深度、学习能力、学习倍数永远不可能超越机器人,那么,学习该怎么办?
不是知识已经不再重要,是重要的知识不会通过被传递了,知识在云端,知识在一个人未知的世界里,那么,罗杰斯说的“凡是可以教给别人的知识相对来说都是无用的”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学习是靠思考得来的,所以,克里斯坦森说“告诉一个人该怎么想比告诉他该怎么做重要得多”,思考最重要,善问者才是善学者,问学的未来也在于此。
所以,近年来在中国学校里发生的教学改革,往往在教学顺序上、教学关系上不断调整,最终大都能够找到一条合理存在的路径,按照学习自然发生的规律,处理好“教师、学生”,“教、学”,“学习、资源”,“时间、空间”,“压力、宽松”等等要素之间的顺序或者关系,从而引发了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升。这都是符合中国文化之道的,那就是找到一件事物的阴阳平衡点,然后去进行合理的组织实施。再进一步说,教学过程就是处理好教学中“学生与教师”、“学习与教学”的阴阳互动关系,何为因阴为阳?何为后何为先?何为从何为主?何为下何为上?何为静何为动?等等。再进一步,这些关系又是变易的,何时开始,作怎样的调整?还是不调整?这就是教学的学问,继续问下去,就是“问学”之道。
二、从“老子法自然”到“后现代情境”
先听一个让我们略显“骄傲”的判断:
辜鸿铭早就说过:在中国人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不管他们多么缺乏清洁的习惯和文雅的举止,不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上有多少缺点,他们依然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赢得外国人的喜爱。 而辜鸿铭给出的中国人之所以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了不起的在于“温顺”,这是“道”的化身。他对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等的比较中阐述了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哪四种?可以再重新梳理一下:博大、纯朴、深沉、灵敏。
细细想来,这四种精神,在《道德经》中都有述及:博大如“道”,纯朴如“赤子”,深沉以“天长地久”,灵敏如“众妙之门”。
老子写完了《老子》,被后世尊为《道德经》,这和《庄子》被尊为《南华经》一样,深远的学问价值需要细细品味。有趣的是,《道德经》里很少写到教学,即便写了,也是“绝学无忧”“不言之教”“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绝圣弃智”之类,看来,老师是反对“学”的,那我们干嘛在教学研究中要涉足老子“道”的世界呢?
曾仕强老师曾经说过,读不懂《易经》,你就读不懂《论语》,也就很难读得懂《道德经》,易经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智慧,道德经是“有无”的智慧,在道德教育里面,我们还是关注这一句话的“有”与“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个“有无”说得很干脆,也很让人震撼,它能够深刻纠正当前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价值判断。
曾仕强老师给出答案:老子认为上德就是我无心,我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不在乎是有德还是没有德,只是重视过程,而不重结果,因为结果是变来变去的。老子要我们顺应自然,凭良心,不执著于德,不总把德放在心上,这样的人才叫做有德。
有德无德在于是否遵循自然的法则,是否真正顺应了自然,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德经》关于“德”的观念与《论语》关于“学”都有一个顺应自然的根本法则,而这个自然法则,就是“道”,就是与《易经》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核心理念相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气充塞、万物关联的特征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学习与道德一体同源,学习也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的发展变化。
人对自然的好奇,人对天地万物的“发问”构成学习的第一动力,老子是不反对“学”的,也不反对“为”,更不反对“有”,只要遵循“道法自然”,就够了。这个自然是什么?“道大,天大,地大,人(王)亦大”,要遵循人的自然。
我们跨过千年,跨过现代社会的种种灾难和流弊,我们寻找一个“后现代”的思维对接,“后现代”一经提出可能就意味着接受批评,它是在基于现代性的批判与自我的批判中建构起来的。因为现代世界并不完美,甚至因为现代化而面临着“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者们有一种批判中建设的“精神风貌”,F•费雷曾说,“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 批判并不意味着“袖手旁观”或者“听天由命”,而是一段重建的历险,这个重建,是重建一个“大花园”,有生命的、有色彩的,超越受制于工业、科学主义发展带来的对人的忽视。
怎么重建?从教育知识观上来分析,现代知识观“由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所代表的现代的知识观,将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视为知识的属性,使得这种知识观具有一种‘绝对论’的色彩。”这种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当然排斥多元,对学习的影响也在于科学理性地接受,学习被认为就是背诵或者记忆。在后现代性的认识论中,“认识被看作是在进行某种解释活动,它要把握的是对象的意义。而意义并非是某种单一的、可一次性解释完毕的东西;相反,它是一个处于不断解释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在不同语境下形成的不同理解来不断生成的东西。” 这样的认识论,更具有人文色彩,更具有人的理解性。怎么解释呢?显然需要老师和学生在教学现场的对话,这个对话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这样,我们就接近了问题的深处,福柯深度剖析对学生的统一驯化,即“操练”造成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消耗而不是促进。标准化授课模式、机械重复的训练、分解细微的要求,高效率、高频率的教育诉求让人的生命性消失了。因为“操练是为了获得拯救而安排现世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西方历史上,它在保留自身的某些特点的情况下逐渐改变了方向。它被用来更经济地利用人生的时间,通过一种有用的形式来积累时间,并通过以这种方式安排的时间的中介行使统治的权力。操练变成了有关肉体和时间的政治技术中的一个因素。它不是以某种超度为终点,而是追求永无止境的征服。” 看一看今天的教学,无处不在的仍然是征服,是对学生问题意识的泯灭,如何回到“学生立场”,我们需要认真探索。
维特根斯坦提出人类社会的“合理性”是以一种“语言游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语言游戏”意味着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它们都是一种对话。什么是合理的呢?用规则来约定俗成即合理,用有价值的习惯生成自然即合理。
在教育领域内,小威廉姆•多尔给出了答案,他在运用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观点、原则、问题与方法考察课程领域后,提出了“4R”说:丰富性(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lation)、严密性(Rigor),意味着课程是开放的、复杂的、转变的,是“丰富的、开放的经验的多层次组合”,是“随我们注意力的转移不断变化中心的复杂的马赛克”, 是由各种交叉点予以界定充满相关的意义网络。 老师是平等因素中的“首席”,学生是平等因素中的“质询者”。
解相花老师曾经解释:为了保证教学过程的高效,必须保证让学生能积极自主反思,积极与文本对话,创造出更多灵感;特别在学生与其他因素作用时有许多交接点,这些是具有催化作用的点,是“保持在学生能力成长边缘上”的点,教师在这些点出现时及时给与正确的干扰,把课堂教学过程引发一种快乐。同时,在不断探究课程过程中,真正的知识或观点不是预设的,往往在“未经探索的联系中”、在“半遮半掩和半透明的可能中”逐渐的创造出来的,课堂充满着神秘。
这就有了问学课堂的有一个实践起点,也是我们课堂一直呈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无为的老师”与“有为的同学”,积极向前的老师与微言大义的老师。课堂上,老师要创造情境并倾听不一样的声音,要听得见思考的声音,听得见内心的波动,听得见思维的涤荡;继而才是学生的有感而发,有疑可问,有对话的产生。
当然,如果绝对化地让同学们每节课都有问题,也是一元式的思维,是不符合不同学科的教学规律的,问学课堂是一种回到“学生为起点”的教学思维方式。科学老师带领同学们提出的假设,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将积聚的感情,英语老师研究设计的活动,数学老师带领建构的知识树,都是以“学生为起点”的问学课程。
三、从“孔子学天”到“人学未来”
孔子说“学天时习之”,就是学自然之道,向天地万物学习。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课堂走上了成熟之道,他们已经录制了两节课,分别是“唐诗宋词的艺术”和“易经与国家复兴”,这两节课分别由杨佳怡老师带领的蒙正班和冯金殿老师带领的明德班的同学们来完成的。
这两节课录制完成后,由国内知名专家点评后,用来供山东省全省的中小学老师观摩、学习。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一所年轻的学校能提供如此重要的教学成果?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遵循自然情境的基本规律,教学就具有价值。而这种价值,也是由传统与未来的结合得来的。传统当然是孔子的教学思想,我们选择以传统为根,慢慢找到了“问学”思维;未来当然是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以“与时偕行”的中国文化来定义未来,这也是“问学课堂”诞生的理由。
我们先来看孔子的教学。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而孔子以“与时偕行”被尊为“集大成者”。
在《论语》中,有一句话往往被人忽视“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杨伯峻先生解读孔子的话:这些山梁上的雌稚,得其时呀!得其时呀!杨先生说:这句话最难懂,他也是勉强地翻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孔子对于“时”的感慨,不管是向往还是伤感,其意义都在提醒我们,“时”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事实上,关于“时”,刘氏逢禄《述何篇》中说:孔子言行皆准乎礼,而归之时中,礼以时为大也。
“礼以时为大”,这样的判断足够惊人,其实,在“益卦”的《彖传》中,孔子早就说过“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曾仕强教授说,益卦告诉我们:要按照益的道理来走,顺应时势来做合理的调整。所以,曾教授给出了我们一个最值得确立的观念:“孔子最伟大的贡献,在‘时’,时间的‘时’。”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何时何地,都要把握一个“时”。曾教授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正本清源的启发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一”,指的就是“时”,时间、时代、时机,审时度势、时不我待、黄金时代,中国人“时”的观念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永葆生机的进步哲学,对这一思想的最大贡献者就是孔子。
由此看来,孔子显然不是复古主义者,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学习教学,更应该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却偏偏愿意回到孔子那里去,我们不成了复古主义者了吗?
还是来看一看孔子的教育是怎样发生的,这里面有没有今天我们“问学课堂”的观念,有没有新时代的教育价值呢?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2•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12•3.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12•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13•1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15•10.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17•6.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
如果愿意,我们能从《论语》中摘出上百句关于“问”—“答”的教育对话。这就是现代和未来教学的答案。
这既是孔子和学生留下的思想遗产,也是启迪后人的教学方法,“仁”是孔子“答”出来的,也是学生“问”出来的,这就是教学方法,学生问、老师答,“问学课堂”的孔子答案。这也是接下来将要详细解读、实践的教学方法。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学生的“问”是怎样产生的?学生会“问”吗?孔子的学生为什么会问“仁”而不会问“道”“大”“富贵”“天气”,这就回到了孔子给弟子们的主张: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勇,也就是今天说的教学“目标”;因为孔子一贯主张“仁者”等等的君子风范,这些风范存在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课程里,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有了问题,所以会引发学习、讨论,然后是问学,这也就是“困而发问”。来看看今天当前的教学,缺少的就是目标、课程,以及学生学习而苦苦不得其解后的问题,于是也缺少了主动寻扎老师学习、讨论的乐趣。
到此为止,我们至少知道“问学”是7000年来中国老师、圣贤教化的一种方式,那么,和人类21世纪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当代世界范围内极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青年才俊的判断: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这位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的理论,对人类社会缓慢进化的现实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时代,很多工业革命时代传统理念会被颠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电脑硬盘、钢铁到重工业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巨头都死于自己最大的优势,它们的错误在于做对了所有的事情。我没有战略可以告诉你,我只有一套理论:我无法告诉你怎么做,只能教你怎么想。”因此,人们需要在既有的固定观念下面需要“破坏性成长”。这种破坏性成长就是用自己的“怎么想”来主导自己的“怎么做”。联系中国千年的思想理念来看,用“想”来决定未来,是从伏羲,到文王周公,到孔子,到儒道承续贯通古今的。作为全球最知名大学的创新理念,中国文化能够给出一个亘古不变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是“问学”。
萨尔曼•可汗:
一位孟加拉裔美国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天才的教育家,有人说他会颠覆人类的教育。他的可汗学院拥有上亿的学生,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学习者之众多超乎想象;有意思的是,可汗学院最初的发起是因为她的表妹娜迪亚,因为娜迪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问这位学霸表哥,而且,后来娜迪亚的许多同学也求教于这位学霸,可汗实在没有时间一一解答,就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可汗学院——把答案放在那里,让有疑问的人去自己找答案,成就了世界最知名的教育机构。这不也是孔子的教育之道吗?可汗说:“学生可能会花费多年钻研某个深奥的数学论题,却未能找到答案;解决某个工程问题的全新方法或许困扰了学生数月,最后却未能成功;学生或许永远也无法为自己的剧本想出完美的结局;一篇诗歌或许枯燥无味,平淡无华。对于这些失败的经历,我只想说:那又怎样?”多好的教育,多好的“问学”之道。我在这里,我在网络空间里构建了一个最大知识学习空间,你有问题你就来,可汗学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深度探索的“问学”之道。
尤瓦尔•赫拉利:
这位耶稣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年轻教授全球瞩目,他是一个敢给未来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他的《未来简史》被我们老师们深入研究,以获得教育的灵感。特别是他给出的人类认知升级的三个公式:
中世纪时期,人类获取知识的公式:知识=经文×逻辑;
这是指读经典书,然后由名师讲解,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长的。
科学革命以后,人类获取知识的公式:知识=实证数据×数学;
这是当前大家诟病的教学,把经过验证的科学知识用科学方法传递给学生。
人文主义时期,人类获取知识的公式:知识=经验×敏感性;
这是面向未来的教学,学生用自己的万卷书和万里路来构建一个敏感性的学习体验,“问学课堂”的意义恰恰在于此。
上述三个公式是非常重要的判断,三个阶段的发展告诉我们,未来的教学靠的是学生自己的经验以及学生的经历。特别是在一个智能化的未来,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能力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是人获取这些知识和能力的思维方式,你想到了才有可能做到,连想都没有想的事情,怎么可能有收获呢?
所以,“问学”才是未来学习的根本。
但是,尤瓦尔•赫拉利作为一位以色列的70后,显然不知道在中世纪以前的远古中国,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学习方法,孔子带着他的学生所进行的学习,指向于“真实情境”,穿越千年,指向未来,所以,教学的传承,也是创新。于是,我们对中国教育有这样的历史判断与时代选择:
先师:通过自然去问道(创造);
后来:通过大师的解惑(创造);
现代:通过课本去记忆(记忆);
今天:通过技术去看见(发现);
未来:通过人对自然的“问道”而开始新的“问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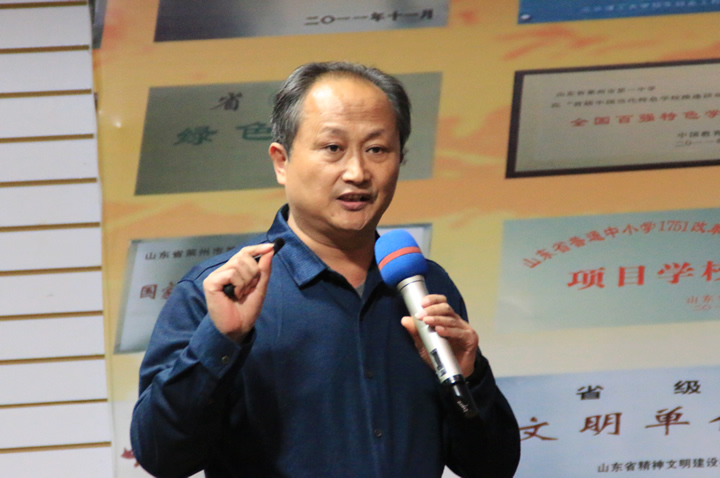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