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 刘少杰 已有0人评论 2017/4/16 9:20:27 加入收藏
地方政府包括一些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甚至挪用专项财政拨款,大兴土木盖“高大上”的政府办公大楼。虽然会提出改善办公条件、方便服务百姓等合理性论证,但其中的符号价值追求是不可掩盖的。常言道:“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如今地方政府为什么会违背这个传统社会的常理呢?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现在官员的流动性差,而在于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的符号价值追求。高大而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不仅象征着牢固的权力和掌权者的显赫地位,而且还表明了政府同企业的区别和同百姓的距离,标志着不可抹平的差别。
不可否认,很多具有形象性的工程并非仅是对符号价值的追求,诸如近年各地纷纷建设的仿古一条街、民族文化村落、历史文化名城等,是集弘扬传统文化,彰显当地风土人情,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功能和旅游餐饮等市场效应于一身的工程,但无论这些工程意义多么丰富,其展现特殊形象、表现不同风格、显示特有含义等方面,都具有符号价值追求的意义。并且,这种区别于同类工程的符号价值,是这些工程能否得到广泛认同的根本标志。而某些地区建设的没有个性、缺乏差别性的仿古或传统文化工程,建后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号价值不明显。
地位在联系中凸显,差别在比较中发现。网络社会空前增强了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无论通过何种形式,一旦接触了互联网或者开展网络交往行为,就会被带入不断扩展又无限丰富的网络联系之中。正是在广泛的普遍联系之中,人们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环境、位置、层次和地位,并且在联系中发生比较、认识差别,进而利用符号表现自身,以便使自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络社会中“不被淹没”。网络社会对普遍联系的扩展同人们对地位差别的认识与追求,具有内在本质性的联系,这决定了网络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推进人们对符号价值的感性追求。因此,尽管对符号价值的感性追求建立在物质丰盛的基础之上,但其大规模扩展或普遍化发展,则应归功于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推波助澜。
三、延续传统的网络化群体
与数字化联系在一起的网络社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为难以直面相逢的人们提供了便利的交往条件,不同阶层或相距遥远的陌生人之间可以开展快捷的缺场交往,新闻媒体和学术界都已注意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有文章指出:“新技术不但让原有的社会关系延续到网络环境下,还提供了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机会。Web 2.0,也即以用户制造和分享内容为特征的互联网交互技术的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合流。对社会学家来说,陌生人的联结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由此生成的社交网络,不但改变了舆论的形态,也影响行动的逻辑。”⑨这也反映了很多社会成员包括一些网络社会研究者的看法——网络化发展扩展了陌生人社会。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使中国的熟人社会加快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中国社会人口、资源与信息的流动,使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高度开放的‘陌生人社会’,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逐渐地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身份关系”⑩。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网络化扩展了陌生人交往空间的同时,原来具有熟悉关系的人们也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大量的网络群体,一个积极参与网络活动的网民可以同时参与几个甚至十几个网络群体,同学群、老乡群、职业群、物业群……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这些首先有了熟悉关系,然后才大量建立的网络群体,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不仅没有在网络化中萎缩,而是相反,在陌生空间中得到了延续与扩大。
笔者认为网络化发展不仅没有促成中国传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而且“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熟人社会”概念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熟悉社会”相比,论者仅仅注意到社会生活表面的变化,而费孝通的“熟悉社会”概念才真正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着力论述的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深入分析的是以感性象征认可的礼治秩序,重点揭示的是轻视普遍原则(法)而畏惧或崇尚中心权势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恰恰都是反映社会本质特点的制度现象(11)。简言之,费孝通论述的“熟悉社会”,是一个在几千年的感性教化下,注重感性思维和感性行动,形成了稳定的感性秩序的传统社会。
哈耶克曾论述了感性秩序的稳定性。他认为理性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理性思维的设计能力和选择能力,理性主义者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自以为是地设计出来的很多规划或体制,通常都不切合实际而被历史遗弃。只有那些通过人们的不断试错行为而形成的感性秩序才是稳定可靠的。“在自发秩序中,为了让人们各得其所,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在调整中产生出秩序的各种规则,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不断‘试验’的结果。”(12)哈耶克的上述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化与现实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金观涛曾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超常稳定性。在金观涛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不是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变化、一切都停滞的社会,而只是说,虽然它的社会结构处于不断的瓦解和重建之中,但从整体上看没有发展到一个新的结构中去”(13)。但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超常稳定,还不能仅从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去解释,而应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深层原因是自殷商周的巫史文化、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春秋文化到秦汉以降直至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文化教化,都是以突显象征、典型、符号、仪式等感性形象为特征的感性教化。正是轻于计算和推论的感性教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注重模仿、从众、延续和重复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并由此保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性。
中国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性至今仍在延续,尽管市场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追求,组织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等从不同方面影响或冲击了中国社会结构,但中国社会的感性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型,而笔者认为这个结论难以成立(14)。如果直面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农村社会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而且城市社会也没有真正实现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变。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各种层面的社会生活中仍普遍存在,正是这些感性的本质特征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具有超常稳定性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会在二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彻底改变(15)。
不仅是感性秩序,对于感性意识、感性行为的稳定性很多学者也都有过论述。马尔库塞关于感觉解放和塑造新感受力的深层作用的论述(16),布迪厄关于惯习稳定性(17)和场域构型作用的论述(18),都触及了感性稳定性的深层根据问题。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就是感性。哈耶克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他从逻辑关系、心理结构和历史演化的多重角度,阐明了植根于经验事实的感性意识、感性行为和感性结构的稳定性。他指出:“习俗和传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无论从逻辑上、心理学上还是时间顺序上说都是如此。它们不是出自有时称为无意识的因素,不是出自直觉,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它们是从这种经验中,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从有关的某些事实或对事物之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而形成的。”(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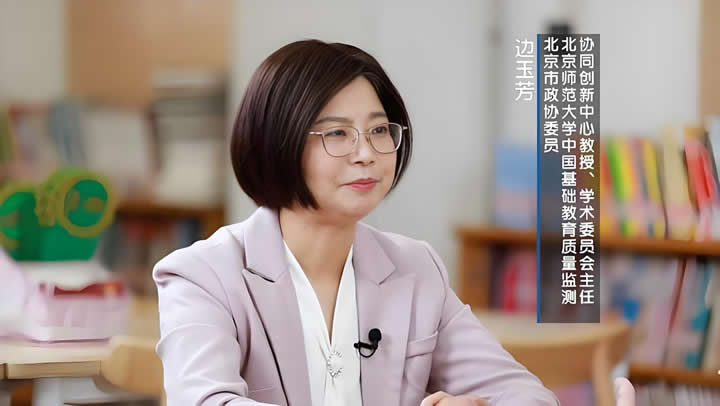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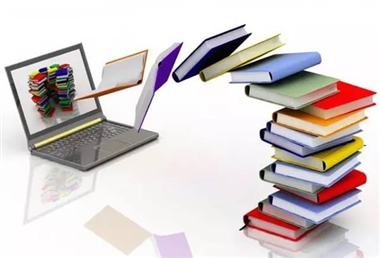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