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展望 作者: 郭华 已有0人评论 2019/9/11 16:26:11 加入收藏
在我国,有“大课程小教学”或“大教学小课程”之说。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到“课程计划、课程标准”的演化,部分地折射出人们对课程以及课程与教学关系的认识的变化。对拉丁语“currere”的理解也是如此。若理解为名词“跑道”,则多主张课程是“预设的”:课程是文本以及文本所载之内容,教学则是实现预设课程的基本途径;若理解为动词“奔跑”,则多主张课程是“生成的”:从学生个人的经验及师生间的现场互动中生成。若为前者,课程与教学相对独立、分离,强调教学对课程文本及其内容的忠实实现;若为后者,教学则是课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课程的实施环节,独立性、生成性、重要性突显,课程文本的强制性弱、弹性强。这两种理解,与塞勒等人所提隐喻的旨趣相似。吊诡的是,“大课程小教学”或“大教学小课程”中的“大”“小”与实践中所呈现的状态恰恰相反。“大课程小教学”中的“课程”无所不包,没有独立的教学而只是课程的实施,但恰恰赋予了教学实践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反之,“大教学小课程”也是同样。关于课程与教学的这两种极端观点,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当代课程视为静止不变的文本,也不能让它超出课程运行的轨道而乱动。”[15]廖哲勋认为:课程与教学在学校教育中各有着独特的价值。“课程是贯通培养目标与学校一切教育活动的桥梁。……‘桥梁’和‘纽带’是当代课程在学校教育活动系统中的定位,教学则是各校贯彻培养目标、实施课程方案的主要途径。”[16]
当然,课程与教学在实践中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极端的主张只是少数,大多数严谨的学术研究都强调二者间的关联。例如,教学认识论指出教学认识客体的重要特性之一是“主体相关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编制以及活动安排要想到是为学生学习、掌握的,因而必须考虑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活动方式,关照学生的已有经验、认识水平,关照教学过程。[17]崔允漷也曾撰文讨论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他提出,要在课程编制中,更好地与教学、教师、学生的要求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其文化选择功能;同时,也要寻求能促使学生吸收课程内容的有效的教学方法。[18]事实上,博比特于百年前憧憬一种新的课程前景时,也是把课程与教学联系起来的。他说:“仅仅记住那些关于事实的言语陈述将是徒劳的。因此,它必须结合着真实的生活情形来训练思维(thought)和判断力(judgement)。”[19]
历经百年发展,我们对课程与教学关系的认识更理性也更深入、具体了,因此,可以预见并期望,未来的课程研究不会在浅层次上辩论“大课程小教学”“小教学大课程”这类问题,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明确各自的独立性、功能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在细节上向纵深推进,致力于探讨课程与教学的内在关联及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具体操作路径。
例如:课程结构的研究要与教学紧密关联。课程结构的设计依然要考虑课程的横向结构——不仅要从客观角度考察相关学科间的内容是否重复、难度是否匹配、课时比例是否恰当等等,还要从主观角度即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考虑横向结构,还要考虑课程的纵向结构,即考虑不同的学科与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之间的关联与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期,景山学校就开始试验课程的纵向结构安排:“课程的结构,不仅要考虑几类课程、几种学科之间横向的最佳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比重,各占多少课时,还应考虑这种组合的比重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学段应有所不同。语文、数学、外语、自然学科、社会学科、艺术学科、体育保健学科、劳动技能学科在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各应占多少课时,这里存在一个如何遵循身心发展的顺序,利用学习某些内容的最佳年龄段来安排课程的问题。……有些学习内容放在最佳年龄段学习,可以事半功倍,过早过晚学习都会导致事倍功半,效率不高。”[20]
又如:要研究同一学科不同内容的教学价值及其教学策略。全面把握学科结构、学科思想与学科方法,确定同一学科的不同内容对学生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研究同一学科的内容顺序与学生发展水平进阶的关系,探讨不同的内容所需要的不同的教学样式,进而再通过教学实践去优化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从而将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真正转化为学生的成长活动、转化为学生发展素养,促进学生的成长。如数学特级教师俞正强就把小学数学的内容分为需要深耕细做、在学生心中植根的“种子课”内容和需要放手让学生自己生长的“生长课”内容,并研究了不同内容所需要的教学样式。[21]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综合
课程研究的百年历程,似乎是一个从理论的、思辨的、经验的研究范式不断走向量化的、实证的研究范式的过程,越来越强调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分析、控制,越来越“科学化”。立于百年之巅,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以为,与课程研究内容的宏观扩展、微观深入相一致,未来的课程研究将涌现丰富多样而综合的研究方法,将出现理论与实验、思辨与实证有机结合的局面。
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方法上的便利,如“大数据”“区块链”,未来的课程研究将会进一步实证化,课程研究的结论将越来越重视证据。依赖个人实践经验的或天才想象的研究,将与大数据的、实验的研究相结合,甚至有从经验、思辨、想象走向实证、数据的趋势。例如,我国中小学常用汉字表的确定,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美国的蓝思分级阅读测评体系,PISA测试以及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正在进行的多国课程图谱研究(content curriculum mapping),我国学者崔允漷所做的“课表”研究等,都是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未必完美,但数字化、数据化、实证化,确实是课程研究的一个走向。
事实上,现代课程研究的本性是实证的。从博比特强调人类经验分析并进行工作分析开始,就奠定了课程论将“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化特质。在这种实证思想的背景下,博比特曾设想课程设计要像设计铁路那样精确。此后,泰勒提出的课程“二维图表”目标分析、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细化、精确化,使博比特设想的“精确”有了具体的样态和现实操作的空间。更早的时期,如19世纪末期,美国就有学者批判了传统的课程研究在满足新需要方面的无能为力:“课程中已积累了很多没用的东西需要去掉。一个长时期,在课程上,用简单增加补充材料的办法来满足新的需要,但没有去掉任何东西”[22]那么,究竟应该增加或删去什么,难以由主观想象来决定,而必须通过实验来确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泰勒将桑代克的课程研究看作是20世纪五大课程事件之一,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他认为:“桑代克的研究使课程建构的本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3]泰勒说:“多年来,有关课程的各种讨论,都集中在不同学科的假定的教育价值以及每门学科在课程中的地位方面。人们相信,学习几何学能使心智的逻辑的官能得到发展;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会使言语的官能得到发展。人们还相信,学习组织严密、难以掌握的任何学科,能训练心智进行合理的思维。……当桑代克的研究表明,修完几何学学程的学生,在解决各种逻辑问题时,并不比那些没有学过几何学的学生好些,以及修完拉丁语学程的学生的英语写作,并不优于那些没有学过拉丁语的学生时,很明显,那种认为课程中各门学科的合理性的传统观点,再也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24]桑代克之所以能够破除误区,就在于他的结论不是来自“信念”也不来自“理念”和“经验”,而是来自于实证研究。
历经百年,课程研究的量化、实证化特征更为突出,而且会越来越突出。
例如,2018年2月12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这个量表“将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三个阶段,共设九个等级,对各等级的能力特征进行了全面、清晰、详实的描述。”[25]“这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26],为客观描述学习者的英语能力提供了一把“能力标尺”[27],为英语课程的研究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性参照标准。这个量表的研制过程若无大量的实证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再以我国《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例。“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字表是在……过去规范的基础上,用更为科学和有效的方法,获得大量的数据,采字和整理字际关系都有较为准确的量化数据作为依据。”[28]历经20年才研制完成这一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确立与发布,对于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课标组组长巢宗祺曾说,“进行汉字教育应该有个定量的标准,要划定一个范围。在这范围里,一般的人得设法把字‘认全’了,在这范围以外,各人可以认自己需要认的字。道理容易明白,然而真的要划这个范围,可并不简单,纳入这个范围的字量究竟多少为恰当?所纳入的应该是哪些字?纳入这些字的依据是什么?”[29]之前的课标研制过程中,“也曾想过要在《标准》里附一个‘字表’,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识字、写字’学习要求的依据。”[30]“《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一级字表’正好可以用到课程标准中去。并且,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组还请研制字表的有关专家再做进一步的工作,将用作语文课程标准附录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的3500个字再分成两个部分,给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汉字教育提供参考。另外,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的基础上,再提炼出一个含有300个常用汉字的《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31]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实证研究对于课程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说明实证研究并不是简单的数据收集,而是长时间、大投入的严谨的科学研究。
当然,实证研究终究只是研究方法,无论是实验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能为课程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但教育目标、价值观,是无法实验也难以量化的,因而思辨的、理论的研究依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类型与方法,教师个人的实践经验也同样可贵。正如博比特做工作分析时需要价值判断,泰勒在确定教育目标时需要有教育哲学的和学习心理学的“筛子”一样,未来的课程研究,也依然需要理论的、思辨的、经验的研究,需要对社会发展趋势、时代精神、社会文化心理的整体把握、价值判断,需要赋予实证研究以精神和灵魂。
课程研究本就是极具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研究,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它对过去成果的选择、确定、转化,它对现实教育经验的提炼与组织,所依据的,正是对未来美好生活和未来美好人生的想象。这个过程,既需要实证,也需要思辨、经验,既要有对历史的追溯、现实的操作,也需要充满浪漫的想象。
正因为如此,所以课程研究魅力无穷。它吸引着一代一代学人,它也会青春永驻,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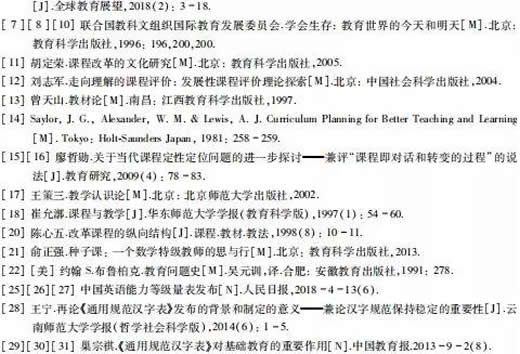
(作者:郭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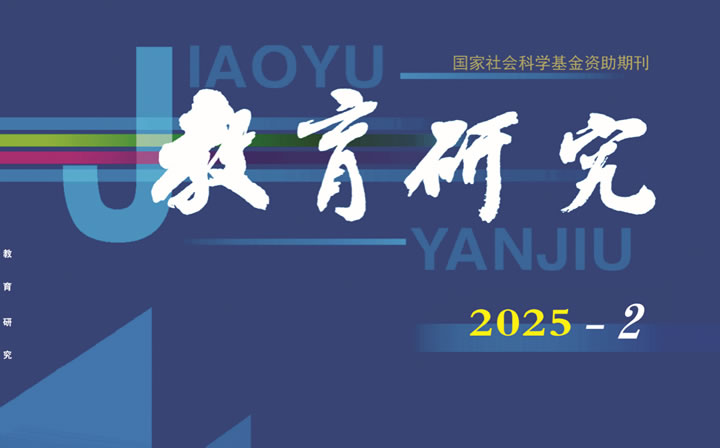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